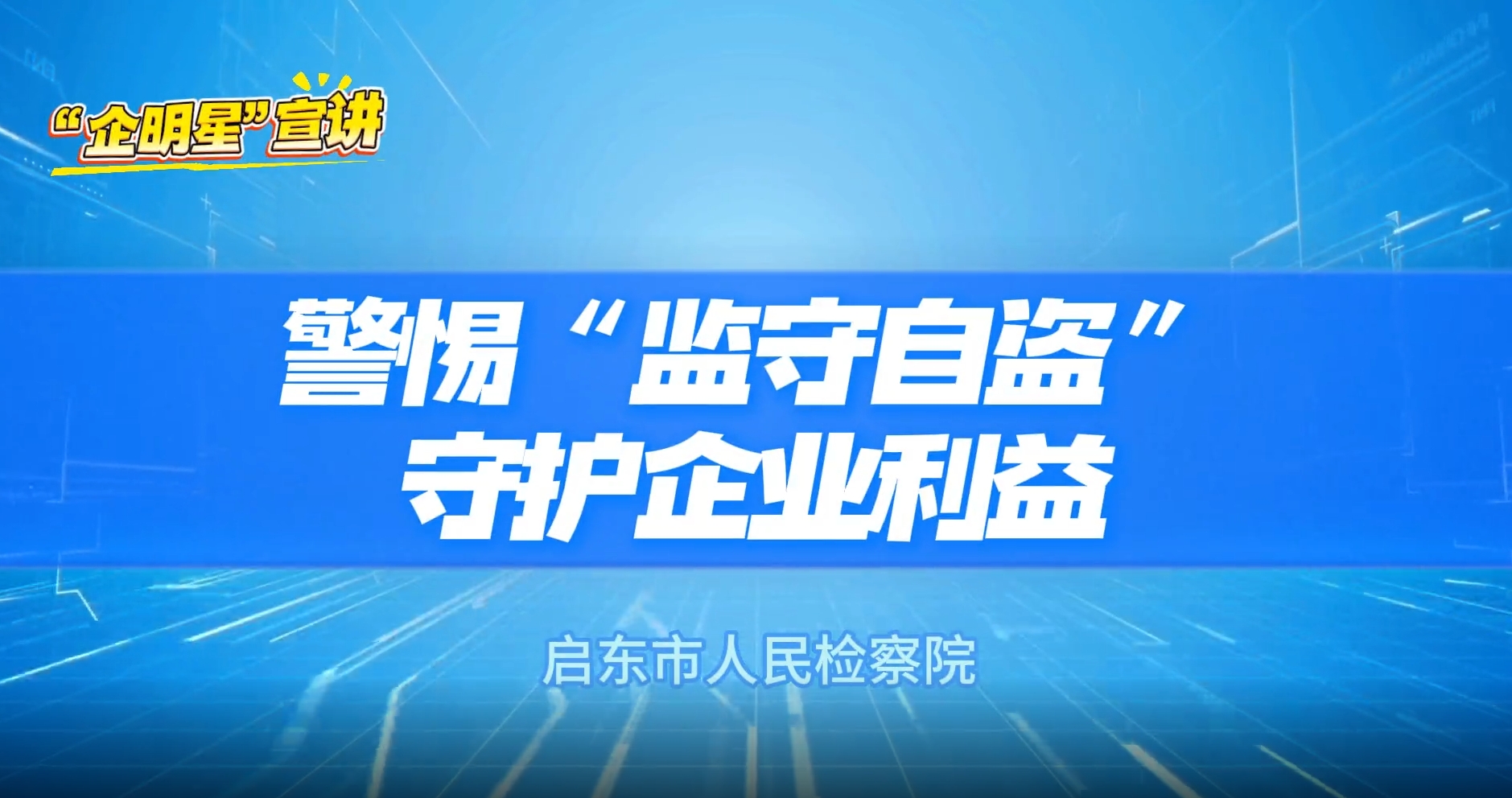传统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官集侦、控、审于一身主动追究犯罪,铁面无情的包公、蓝鼎元等司法官动辄大刑伺候,迫使犯罪嫌疑人尽吐真言,往往赢得人们尊重和信赖。自晚清以降,这种纠问式诉讼,特别是刑讯制度不仅成为西方实行领事裁判权的借口,更推动了“变法救国”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1906
年,检察组织首次出现在第一部法院组织法《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中,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确立了国家公诉制度。清朝覆亡后,清末移植的检察制度为民国所承袭。
传统侦查权由此受到检察权的有力制约,并逐步向现代侦查转型。“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悔”,古代刑事司法强调迅速对犯罪予以报复和制裁,以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控制;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被视作查明案情的手段,不仅可以“勾摄”“讯”“待质羁押”,还可以“拷讯”。缺乏制约的侦查权极易被滥用,“借传讯邻证之名,扰及同村居民以邀原贿,若有殷实之家,但在数百里内者,必百计株连,指为邻右,名曰飞邻”。清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侦查权滥用的残酷现实,1906年的上谕称:“各府、州、县或严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动辄株连,传到不及审讯,任听丁差蒙蔽,象肥而噬,拖累羁押,凌虐百端。”
1907年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了侦查程序文书、侦查主体、侦查权限,对各项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了约束,如侦查人员必须获得检察官签发的厅票才能逮捕犯罪嫌疑人;“经搜索未发现应扣押之物者,应付与受搜索人以证明书”;“被告羁押之处所,检察官应随时视察”。1910年的《刑事诉讼律》(草案)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必须获得传票、拘票、押票等法律令状,“检察官、司法警察官侦查或预审中,非有地方检察长或预审检察官之拘票不能拘摄被告人。”检察权对侦查权进行控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是公诉的基础和前提,侦查的质量决定了公诉的质量与结果,只有确保侦查活动合法有效,控诉职能才能合法有效行使。正如民国学者指出,检察“于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之义,关系重大”,检察权对侦查权的约束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促进了诉讼文明,使刑事诉讼照进了人文暖色。
检察权注重自我克制,以“知止”传达司法善意。“知止”常见于经史百家,孟子的“可以止则止”,老子的“知止不殆”,均表达了一种就是“适可而止”“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的思想。然而,传统刑事诉讼一旦启动,必将引发以下连锁图景:鸣冤、告状、抓人、刑讯、定罪、判刑,即使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疑罪,也应“罪疑唯轻”予以处罚,历史上的缇萦救父、赦免等做法,宽免的是刑罚,而不是诉讼程序的终止。
检察权的诞生让刑事诉讼有了“知止”的可能。民国初期采起诉法定主义:“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对确无证据证明有罪的案件,检察厅应不起诉,如《直隶省各级检察厅办事规则》规定:“告诉告发事项及由各衙门送案者业经详细讯问并无犯罪情节,得决定其免诉”。1928年《刑事诉讼法》和1935年《刑事诉讼法》采用起诉便宜主义,赋予了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对于无证据证明犯罪的、证据存疑的以及轻微犯罪的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司法的谦抑性。数据显示,1928年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率为58%,1935年酌定不起诉率约为63%,检察机关克制入刑、重刑主义冲动,“适可而止”“有所不为”,关注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为刑事司法注入了温情的人文关切。
检察权的演进有力促进了刑事格局由传统的“追击”型向两点抗衡、一点裁量的对抗型转变:一方面,被告人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诉讼主体,“凡审讯原告或被告及诉讼关系人,均准其站立陈述,不得逼令跪供”。从“跪”到“立”仅有一字之别,却扭转了长期以来官老爷高坐大堂,被告人等涉案人员匍匐跪地的传统做法,张扬了被告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告人逐渐拥有了与国家权力抗辩和理性交涉的能力,诉讼民主、诉讼文明、诉讼人道的理念得以张扬。
另一方面,检察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约促进了司法公正。担任控诉职能的检察组织出示证据、指控犯罪,法院对证据不足、证据不合法的起诉可以反对,最典型的反对方式莫过于判决无罪。审判权制约检察权的同时也须受检察权制衡,如审判须遵循不告不理原则,这不仅意味着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还要求法院的审判范围与起诉的范围相一致;再如检察组织通过抗诉方式监督审判权,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在大理院二年非字第六〇号案中,被告人为防卫妻子被掳卖,将纠众持械入室的侵害人刺毙,一审认为被告人不构成正当防卫,经检察机关抗诉,大理院撤销原判,改判被告人无罪。
知往鉴来,在检察权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检察制度时断时续,时依附时独立,凸显了检察权诞生、萌芽、发展的进程。回眸检察制度演进的曲折历史,有利于找准检察权在诉讼活动中的定位,厘清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正如志田钾太郎博士指出:“中国改良司法,实以设立检察制度为一大关键。”检察权的有效行使才能推动传统粗放式司法向精密化司法的历史转型,更好地保障人权、促进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