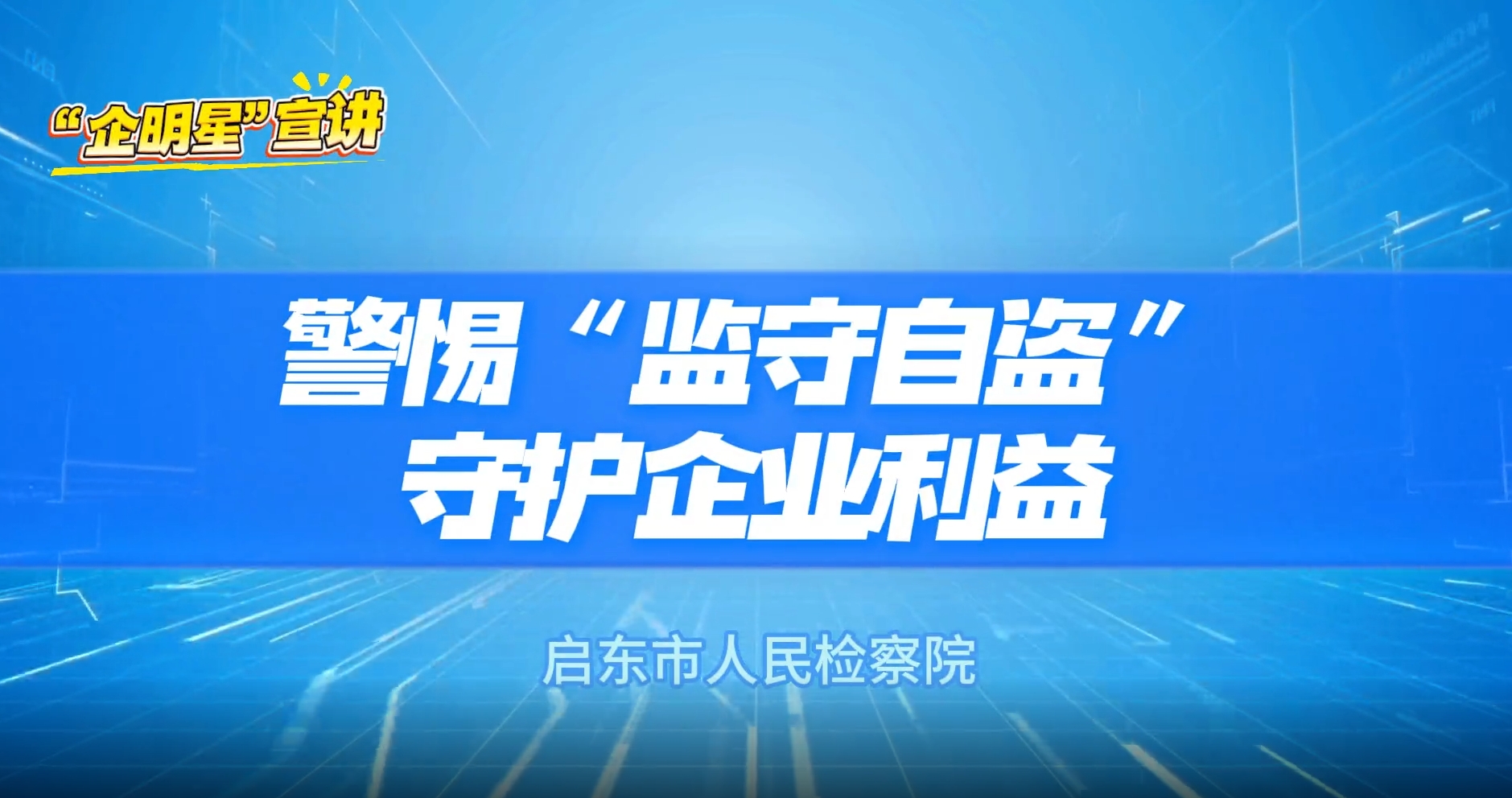《明朝那些事儿》有一段不出名的小人物张子明的描写震撼了我:张子明给陈友谅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呆子,站在那里,手都不知往哪里放。这个人容易对付。陈友谅开始给张子明做思想工作,从拉家常开始,到天下一统、民族大义等等,张子明只是不断地点头,到最后他也说烦了,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我合作,诱降洪都,你就能活;不合作,就死。
张子明忙说,我合作,我合作。于是,陈友谅派人押着张子明到了洪都城下,让他对城内喊话,让城里的人投降。张子明连声答应,走到城下,大声喊道:“请大家坚守下去,我们的大军马上就到了!”陈友谅傻眼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柔弱的读书人有这样的胆量,气急败坏,抽刀杀了张子明。他这才明白,这个书生并不怕死,只是他的使命没有完成,他还不能死。他还一直记得张子明临死前那嘲弄的眼神。
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闭上眼睛,仰起脸,把涌到眼眶里的泪水忍回去。柔弱与勇敢,竟是以这样的形式共生于一个书生的身体与灵魂之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然而他依然选择了死——只为了更多的人能活下去。
每当读方孝孺《闻鹃》中“忆昔在家未远游,每听鹃声无点愁;今日身在金陵土,始信鹃声能白头”的诗句,总有一种深重的伤感和同情。他以儒家的入世的积极态度抗争到死——即使被灭十族,也绝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虽然我并不讨厌朱棣,真心认为他皇帝当得不错,但是当他下令诛杀方孝孺并灭其十族时,仍忍不住嫌他没有曹操的胸怀。
我却始终保持着对“故纸堆”的热情。因为我始终相信,在那些充斥着流血、屠杀、成王败寇的文字后面,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将永远存在。叔本华在其名著《爱与生的烦恼》里说,历史的人性和历史结局本身一样终极都是指向悲剧性的。古希腊的悲剧美学和鲁迅先生都认为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五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描摹了这个主题。史书里也有不少成功和掌声的盛宴,盛宴中英雄主人公在希望的荣光里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但待宾客作鸟兽散后,今夜也许只有一弯残月西斜,那些踌躇满志的主人安在?
鲁迅说:“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的话就是我的历史人性观。有希望终归是好的。因为,我对历史人物里的人性始终是抱着“性本善”的目光审视的。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盛宴之后,泪流满面!”每每品读这句颇有古风色彩咏史诗句时,就使我的心灵深深震颤!但我震颤的是,那些悲凉悲剧背后的人性大爱和那一道道平凡历史人物的演绎的“真善美”风景。
我的恩师,清史学者、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曾对我说:“在复杂的历史人性中,你可以瞥见今人的善良脸庞和良心脉搏。”其实历史人物和今天每个平凡人一样,都无所谓纯粹的高尚和庸俗、唯美和丑陋,它只是一部人群的人性史,当然里面也夹杂着一些末枝的所谓“历史人物”的帝王的家谱史和官僚酷吏们的权欲史。我真正想读是却是一部平民和小人物的柴米油盐史,因为唯有这些篇章里才不时地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说:读封建历史我看不见个体的中国人,在“酱缸”周期循环里,尽管每个人都是牺牲品和衍生物,但他们还是坚强而骄傲地活着。因为,他们是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因为一部《二十四史》掩藏不住人性的光辉,因为这个民族叫中华民族。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相信人性。”我想起了当年明月的诗句。我想说:读历史,耳畔总有一种抽泣的声音在回荡,在一片片大英雄人物的倒塌声中,我心中总有一缕激昂和忧郁的双重情愫缠着我的脚踝,使我举步维艰。刹那间我的爱、善、真、美、忧患、责任、哀伤、深沉感全数袭来,仿佛要将我顷刻撕裂!
读史,仿佛在一堆堆废墟的烟尘里瞥见了我们每个人的前世今生,在一个个平凡人物的微笑里站立起一个个深情的人,率真的人,坚韧的人,唯美的人,热爱生活、热爱真理正义和大自然的人,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坚实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