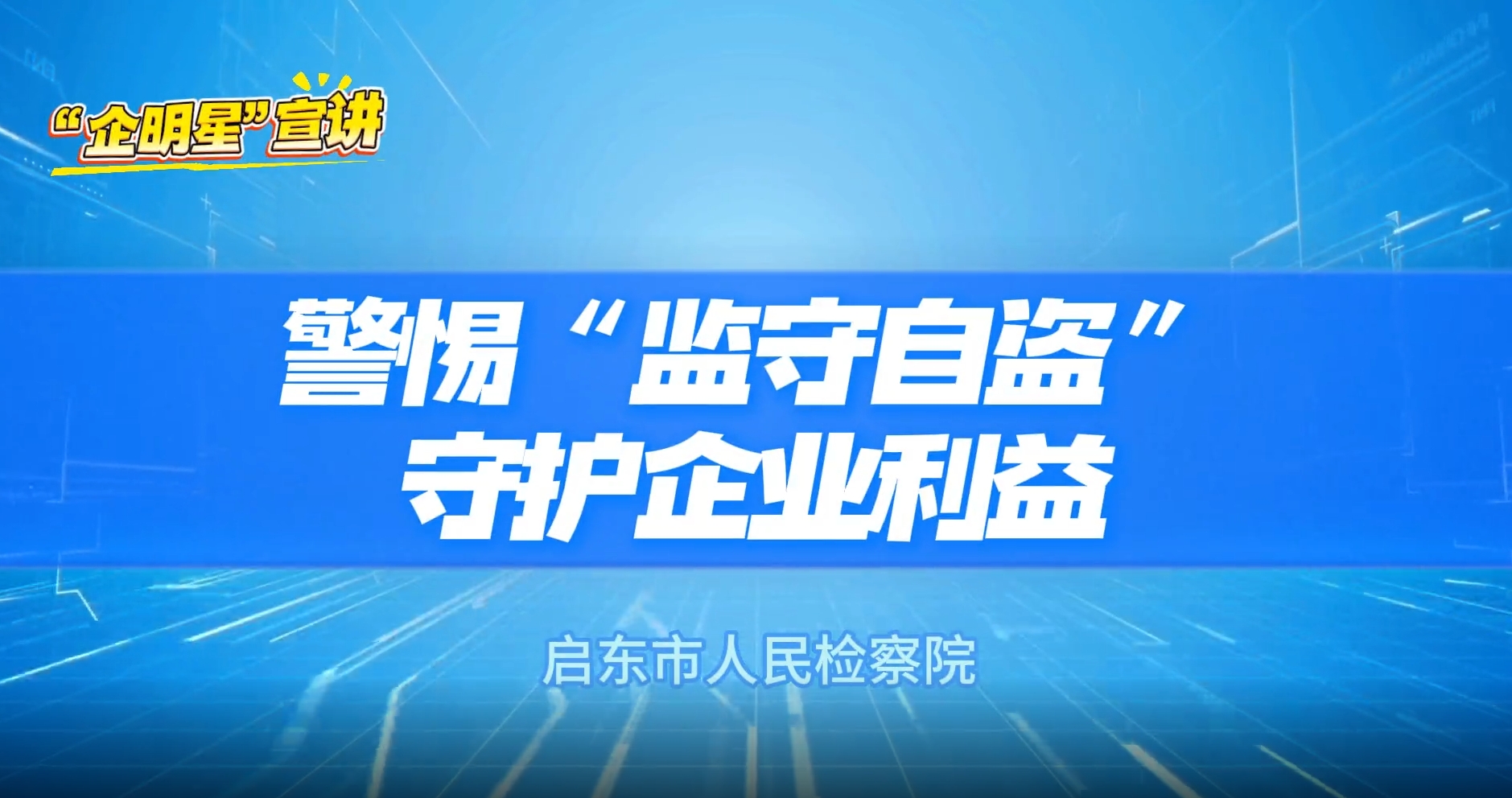文/刘羽蕴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观点摘要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举了两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的情形。但在一行为形式上符合《意见》所规定情形时,仍应具体把握该行为是否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
作此分析时,应遵循同类解释原则,对手段行为危险程度上是否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具有相当性进行衡量;应有别于抽象危险犯,对行为是否直接、紧迫、高概率地对多数或者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等造成具体危险或者实害进行判断;亦应对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是否为故意等方面进行把握,并注意与故意伤害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罪名的区分。
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两部意见),意见明确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下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列举了两种具体情形。
两高两部意见规定,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以下简称确诊患者)、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以下简称疑似患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该如何理解上述规定,行为人实施了该两项行为,是否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应当注意到,上述规定勾勒了在当前疫情期间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常见模型,即指引司法人员在遇到该两种情形时考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入罪,但符合此两种情形是否即构成该罪,还应当具体分析该行为是否契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质内涵。比如,确诊患者拒绝隔离治疗,进入公共场所,但该场所因疫情而人迹罕至;确诊患者擅自脱离治疗,为回家戴好口罩、护目镜等防护设备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等情形是否应当认定为本罪等问题,还是须就该罪犯罪构成进行把握。
一、是否属于“危险方法”——要求手段行为危险程度的相当性
首先,应当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危险方法”。《刑法》中对危险方法的规定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根据同类解释的原则,“危险方法”应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在手段危险程度上的相当性。要达到手段行为危险程度的相当性,应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考量:
其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具体危险犯,其手段行为必须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公共安全之上具体的危险。至于这种具体危险的程度,虽然在理论上对于《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一百一十五条第1款的关系有基本犯——结果加重犯、未遂犯——既遂犯等不同解读模式,但都不影响将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与第一百一十五条第1款中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实害后果建立起关联,正如劳东燕教授指出,第一百一十五条第1款中的结果应是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危险的现实化。
其次,从性质上来说,成立“其他危险方法”必须具有一定时间段内导致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广泛危害性或者迅速延展性。即该行为必须是如放火、决水一样同时产生了对多数人的广泛危险或者这种危险状态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展。
再次,此种危险方法对于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而言,应当具有高概率性及紧迫危险性,这也是该罪作为具体危险犯,有别于抽象危险犯,必须具有由危险状态转化为现实危害的高度可能及紧迫危险所决定。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播性极强,传播途径包括直接传播、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等,在已经确诊的病例中,不乏有人无武汉接触史,仅是与患者在同一超市、市场采购即被传染的例子,可见确诊患者、疑似患者、病原携带者进入公共场所的行为,有相当可能会使得同样出现在该公共场所的多数人被感染,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具体、紧迫、广泛且高概率性的危险。
故而,按照上述对于危险方法的认定标准,确诊患者、疑似患者、病原携带者违规进入公共场所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符合“危险方法”的内涵,新出台的两高两部意见作此认定并无不当。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特殊情形,如文章开头所举确诊患者违反规定进入因疫情而人迹罕至的公园等公共场所的例子,由于其行为并不会产生具体紧迫的危险及高概率性的危害结果,不应成立本罪。
二、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兼论与故意伤害罪之区分
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指出:公共危险罪是侵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的犯罪。其中多数属于抽象危险犯,是故一般不会与人身犯罪和财产犯罪发生重合。而我国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多是具体危险犯乃至实害犯,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即是如此,故该罪与人身、财产犯罪都会存在竞合,区分罪名难度也就显著增加。
那么,如何界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故意伤害罪等人身犯罪呢?此时,需要着重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特征。
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理解,刑法理论上素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该危险须涉及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涉及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即为公共危险,不需限定为不特定人。第三种观点认为该危险须涉及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安全。第四种观点认为,该危险须涉及不特定并且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安全。
我国刑法理论历来持第四种观点,即认为需要对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造成危险。但近来第三种观点亦在壮大,如张明楷教授等即认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均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内涵,因为刑法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目的是以个人的生命、身体等法益抽象为社会利益作为保护对象,故应当重视“公众”及社会性,而公众与社会性势必要求重视量的多数。
本文亦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该罪区别于其他人身、财产犯罪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其将抽象、整合的社会利益而非具象、单独的个人利益作为保护法益,而社会利益本身即蕴含“多数”的要求。同时,笔者认为是多数而非不特定构成社会利益核心特质,但“不特定”作为一种补充,通过补足在犯罪行为实施时侵犯对象无法确定、危险随时可能扩展并危及潜在多数人的情形,周全了该罪名对社会性法益的保护边沿。
两高两部意见中,将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行为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即体现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与人身犯罪的这一区分,即针对特定人的权益侵害以人身犯罪而非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在抗击“非典”期间,亦有观点提出,不能仅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的直接指向来对上述罪名进行区分,而应结合突发传染病疫情的传染性特征作具体分析。即使行为人只想把“非典”感染给特定的某几个人甚至是某一个人,但因为“非典”的传染性极强,不可避免地会使疫情进一步扩散或者有进一步扩散的危险,从而最终危害公共安全,也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上述观点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样依赖于危害结果的“二次扩散”“次生灾害”来认定对公共安全影响的论点,会将危害公共安全的概念进一步不合理地扩张。以“多数”为核心来界定是否危及公共安全,应就行为本身在客观上即具有对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的直接危险性而言,而不能就行为的间接危险性而言。
此外,如果行为人对多名医务人员撕扯防护装备,即使行为最终导致多名个体感染病毒,也不能认为一定是危害了“公共”的安全。因为行为人实际实施了数个同种行为,就每个单一行为而言损害后果具有有限性,并不具有同时危及多数人安全或者随时向危及多数人安全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而是涉及成立同种数罪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确诊或者疑似患者、病毒携带者拒绝或擅自脱离隔离,未采取防护措施在公共场所对医生实施撕扯防护装备等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的行为,则会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是寻衅滋事罪竞合的问题,在此不再展开。
三、主观方面是否为故意——兼论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区分
两高两部意见第一条在列举了两种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情形后,规定: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对比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针对当前疫情防控所新增的“定点”罪名。该罪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规定,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均可纳入该罪规制范畴。新冠肺炎虽然不属于甲类传染病,但是属于国务院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实施的其他需要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故对引起其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亦可纳入该罪评价。
两高两部意见中,将列举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的两种情形外的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防控措施的行为,同时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传播严重危险的,规定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处罚。但如前所述,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除了意见列举的客观行为表现外,还须结合该罪的其他特征进一步考察。故对于拒绝执行防控措施并引发新冠病毒传播或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笔者认为亦不可生搬意见规定进行一刀切,除了意见规定的客观方面表现的区别,还应当结合该两罪的其他特点予以区分。
显而易见的是犯罪主体的区分,两高两部意见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形中,主体应是特定的自然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病原携带者及疑似患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应为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更值得注意也更易被忽视的,则是主观罪过形式的区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并无争议,显然只能由故意构成,即明知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并有相当概率产生危及公共安全的结果,仍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然而,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学界历来有多种声音:第一种观点认为该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甲类传染病或者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严重危险而故意为之。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可以为故意,也可为过失。第三种观点也即通说认为主观方面应是过失。
笔者赞同通说的观点:一方面,该罪最高法定刑与大多过失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一致,立法原意应为过失犯罪。另一方面,该罪是因行为违反行政法规达到须科处刑罚处罚之程度而被刑法纳入规制,可类比交通肇事罪,应同属过失犯罪。而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和过失的规定, 我国是以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态度而不是以其对行为本身的认识和态度作为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标准的。
就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构成该罪的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违反传染病防治规定可能是明知的,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或者传播的严重危险应当持过失。故主观方面属故意还是过失,可作为区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要点之一。
回到前文所举确诊患者擅自脱离隔离,为回家取全套防护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例子,患者的行为可能是对传染病防治规定的故意违反,但很难说其就一定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故不宜直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盖棺定论。
值得思考的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 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 情节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 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而在新出台的两高两部意见中,并未提及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前所述,主观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是区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重要方面,那么在新意见出台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关于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并过失引发疫情传播或者是传播严重风险的行为,是否还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空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又应如何将其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区分?此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