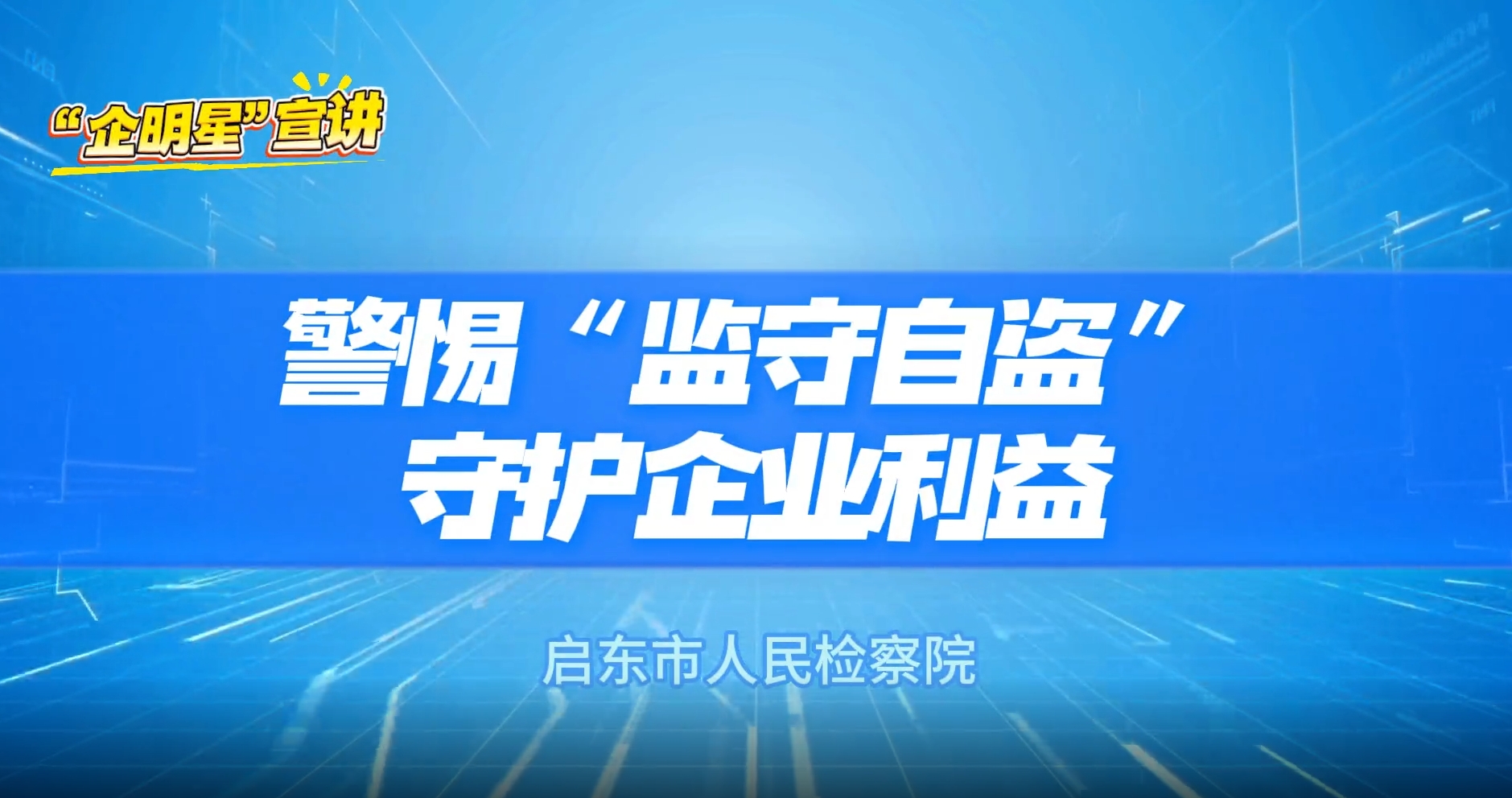第一次读到“黛青”这个词汇,是在《红楼梦》第七十九回:“如黛青眉,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一见便喜欢起来。因为它,与蒙古语里的“乌嫩青柯尔”十分相似。乌嫩青柯尔:即是云青的意思。这个词汇,可以表述故乡山峦的真实色彩和情状。唯山地草原上的山峦,才配用这个词汇,地域开阔,天空高远,而气流清爽。譬如:蒙古高原。唯有百灵鸟青郁的叫声,和蒙古马长长的嘶鸣,才可完美表述它的高阔与情致。就如席慕蓉在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里所写: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的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泪落如雨。”
她还写:
“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中有一首歌。”
的确,蒙古高原与蒙古人血脉相连。一见黛青色的山峦,心中便有了依托。感谢雪芹先生,他把这个词汇教给了我。仅仅一个词汇,如此让人刻骨铭心,是我始料不及的。或许是因为,它让我寻到了描绘故乡山峦,神似情状的缘故。
还有一首蒙古族现代歌曲,它以清丽的歌词,悠扬的曲调,让人心驰神往,其中,有两段歌词是这样的——
“高高蓝天的镶边上,
那是我黛青色的山峦。
遥望那心中的福地,
那是我心爱的故乡。
闪亮在遥远天际的,
那是我银色的包房,
亲爱的妈妈手捧着鲜奶,
留在那朦胧的远方……”
我把它译成汉文时,就借用了黛青这个词汇。我们一帮作家诗人,彼时正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一处大型蒙古包里,喝着飘香的奶茶,品尝奶食和塔拉哈。塔拉哈,即列巴,为主人自制,好吃到无法形容。
时在七月,地蒸气在闪闪烁烁地上升着。山峦横卧,美若一道天然蛾眉。我想到了吴冠中。天空蓝得出奇,草地浓绿得流油,几片羊脂云,移动其间,是刚点到的那一笔。《诗刊》主编、诗论家杨子敏提议,让我再用蒙汉两语演唱那首《故乡的倩影》。我拿起哈达,托着奶酒,开始献唱:“高高蓝天的镶边上/那是我黛青色的山峦/遥望那心中的福地/那是我心爱的故乡//闪亮在遥远天际的/那是我银色的包房/亲爱的妈妈手捧着鲜奶/留在那朦胧的远方……”唱毕,大家沉默片刻,继而送来热烈的掌声。其中,有几位诗人动了情,抹了泪。子敏兄,尤甚。不是歌者优秀,是歌曲情深意切。
雁群南来,也正好掠过头项,鸣声若雨。左前方,在淖尔里饮水的那一群良驹,不时把嘶鸣亦传递过来。还有,包门外逶迤而去的各色野花,在风中轻轻地摇曳,在作扭动状。噫嘻!七月的呼伦贝尔,果真诱人亦醉人啊。说它是仙境,也不为过。子敏兄,具有音乐天赋,他掏出采访本,让我哼唱,他记谱亦添词,之后,自顾自地哼唱起来。后来,驰向大兴安岭的漫漫旅途中,满车箱都是《故乡的倩影》的歌声了。我对他说,我心中的确装满了故乡,吟唱时眼前出现的是我白发的慈母,和充满泥土味的故土。
故乡,自古至今,是每个人心中深深藏匿的那一粒珍珠,且带有体温。那些,有关故乡的古典诗词,一触让人动容,是因为心中藏有乡愁的缘故。如:“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等等。乡愁,历来是言不尽意的一种诉说,是永不能治愈的病症。人犯乡愁症时,总有一个物象,首先撞进心来。如我者,则是那一脉——黛青色的山峦。那是我落生之后,第一眼看到的象征物。后来,苦于找不出恰当形容它的汉文词汇。与一个黛字,加一个青字,相遇即是大半生。
养育我的那个村落,叫做嘎亥图艾勒。艾勒,即村落。是一处狭长的盆地,四面环山,一条小河,挨村流过。人称:嘎亥图高勒。高勒,即河。嘎亥图,蒙古语:有野猪出没的地方。童年故乡的山野,常有野猪出没,有时成百上千。假如不守防,一片苞谷地一夜间便荡然无存,颗粒无收。我即是敲着铝制脸盆,去赶野猪的那个少年。巡夜中,夜露打湿裤腿,感到生疼,但是觉得兴奋。那种敲打脸盆的声响,在静夜里,震动四野,甚觉威风。困,是一定的,也饿。于是,与同伴们烧起青苞谷来吃,那种飘满山野的清香,至今让我发馋。然而在那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没心没肺的不知珍惜。后来突然有一天,被人呼为异乡客,或游子时,才明白,那一脉黛青色的山峦,和敲着脸盆赶野猪的童年,离我远去,已变得如梦似幻。方才知道,自己已非山野里游荡的那个野孩子。那些透明的山雾,闪烁不定的绰绰山影,山上出现的海市蜃楼,远方城市的倒影,以及移动中的车水马龙,都早已变为往事。清夜里,随我而眠的,只有两行浅浅的思乡泪。
后来,卸下马鞍,脱罢征装,白发覆额之时,乡情,却不知不觉间发酵起来。于是,千里万里,奔回故土,急切地去寻亲寻根。当远远望见那一脉黛青色的山峦时,心似乎圆润了,然而,顷刻间又破碎了。因为,为我升起那一缕,招魂般炊烟的,已非我身着长袍的白发慈母。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印着胎记的饸饹面,不再香香地在等我。于是,黛青这个词汇,开始在记忆里模糊起来,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忧伤,随之刺痛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