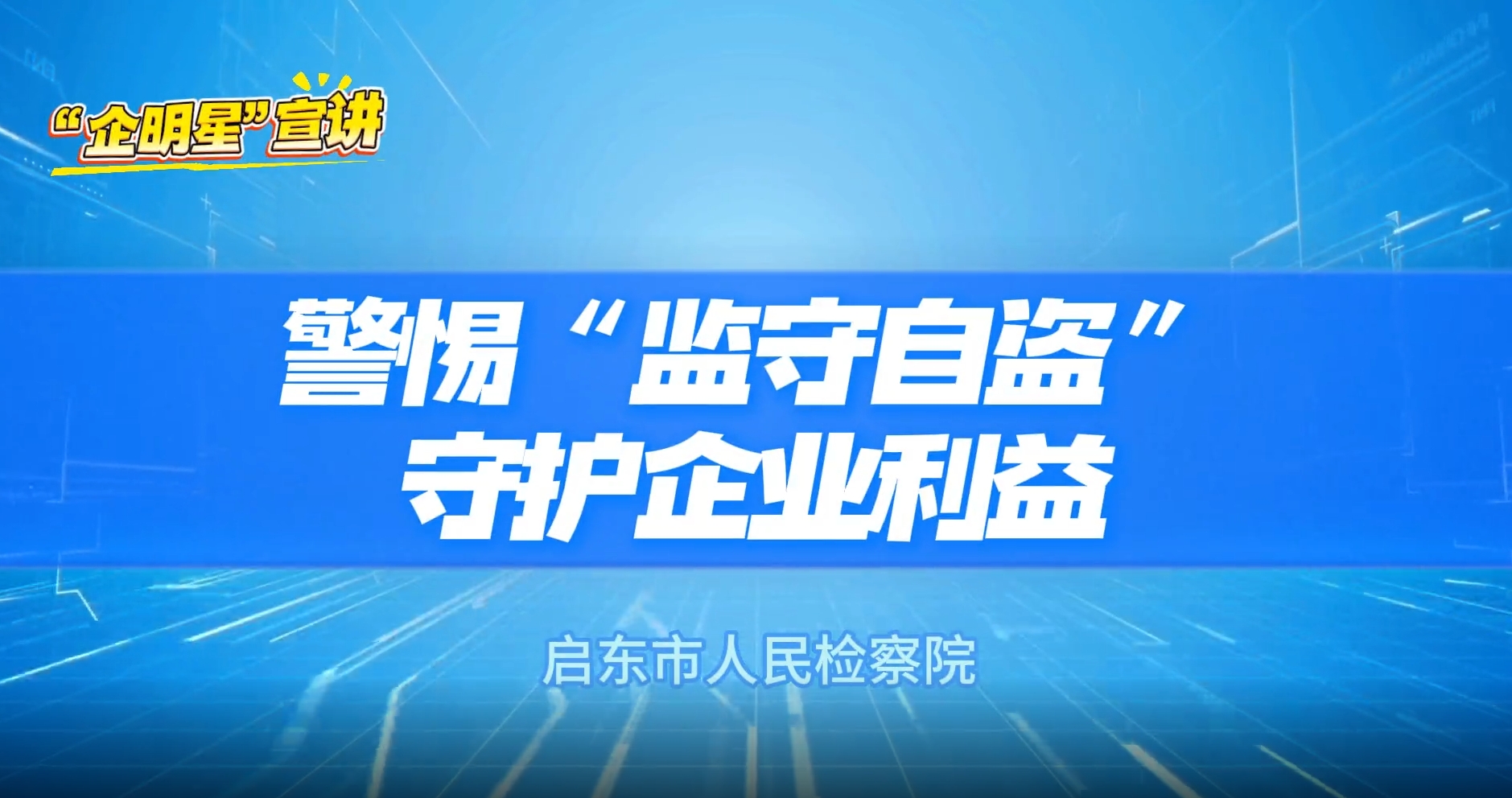故乡有一片原野,水草丰盈,野花竞美。蓝天白云倒映在清澈的池塘,里面的鱼、虾、野鸭、白鹭仿佛在云天里悠游。还有一条河由北向南,流入渤海。这里有我童年的故事,少年的身影。步入老年,偶梦童年趣事。
也巧,童伴小春打来电话:“五哥,村东的万亩果园开花了。我看着苹果花,想着你们,年年如此。40年不见,‘青春作伴好还乡’啊!”乡音激荡,不容我说没空。
我们走进苹果园,在热闹的花潮里游荡。小春说:“南方的养蜂人帮了大忙,不用人工授粉,能省很多钱……”我躲闪着在花潮里忙碌的小蜜蜂,一行诗句从远方飘来:“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们一路聊着,“五叔!我们来啦!你们在哪里?”听到小明的呼喊,我们异口同声呼应:“被红裤衩绊个大前趴那个地方!狼不会来了!”我们的笑声碰撞到一起,砸在苹果花上,飘零的花瓣,流进我们梦里童年——
几只叫天子爆发戾气,那撕肝裂肺的怪叫声令人胆寒,它们在空中盘旋,俯冲,对嬉闹的我们展开攻势。我焦急地说:“小春小明,赶快放飞手里的雏鸟!当心它们的爸妈啄瞎你们的眼睛!”小春反驳:“你嫉妒!你没有抓到小鸟。”“我抓不到鸟?”
突然,东河对岸传来沉闷的嗷呜,引起我们恐慌:“快跑!狼要过河。”我惊呼,扭头向村子方向奔跑,边跑边脱下火红的背心举过头顶,呼啦啦地舞动,“把红背心、红裤衩都脱下来,举起来摇晃。狼怕火!”他们放飞小鸟,追随着我,惊得野鸡、鹌鹑扑棱棱地贴着草梢飞行。小明气喘吁吁,边跑边脱红裤衩,脱到脚踝处时,摔个前趴,压倒一片蒿草。他哭喊着:“狼来了!你们等等我呀!”哭声把原野搅得不得安宁。
放牛人方叔光着脚闻声跑来。他说话口吃:“啊哈,啊哈,孩子们别怕!那是狼吗?狼在夜里出没。”
我们淹没在一片蒿草丛中。几团红红的“火焰”向村子方向游动。
故乡在辽河下游平原,“风吹草低见牛羊”也是半个世纪前,我家村东20多万亩原野——成群牛羊在这片原野上肥壮,总有几匹马几头驴在这片原野上嘶鸣,孩子们在这片原野上健康快乐地成长;东一棵西一棵婀娜多姿的弯杨曲柳,放牧着这片原野。
春季,好多无名野花从草丛里探出头来。女孩子喜欢花,跟在男孩子后面,挖了满满一筐野菜后,哪个颜色的花朵也不放过,样样采几枝,用毛草捆成一大束带回家,插在水瓶子里,摆在柜盖上。
在果园里,我们寻找蓝雀儿花、棉花花……唉!蓝雀儿带着数不清的野花“飞走了”,少见的几棵紫地丁、蒲公英、马兰花,匍匐在林台上。
我们带着童年的兴致,走过这大片果园。小春说:“喜庆吧?”我感叹:原野变田野,开心!我恋旧。
黄蒙蒙的田垄展现在眼前,刚钻出地皮的小苗无精打采地蜷缩着。“科技是生产力。新品种耐旱,亩产是50年前的3倍多。”小春的话令人释然。
外县人管我们这里叫“下洼甸”,小时候,牛蹄洼里的那点水都有鱼秧子;嗯,如今干旱成沙,气候变了;是呀,少见蓝天白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我说,到东河看看去?小明说:“好。继续寻找我们的童年。”
短短的身影在脚前引导我们,奔向那条委婉吐翠的绿色曲带。“那是大堤,离东河不远了。”小春告诉我们。“记得,记得。”我连声回答。这片养育我18年的家园,哪里有池塘,哪里有桑榆、野果,连小路边那几棵老树的模样都根植于心。
我们走上河堤,不忍心踩踏低矮堤坝上的青青小草。巡看东河,黑色的河床耕耘成田垄。田垄上,裸露着好多被风化了的贝壳泛着灰白的光亮,像骷髅的嘴,不再言语。
我上小学时,《歌唱祖国》的歌声从校园里飘向这片原野。村东头立起十字木牌,横担上写着“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社员、学生,打着红旗,扛着铁锹,挑着水桶,开进这片原野。随坡就岗,植树造林,“原始植被不得破坏!”上级指示。
又是一年芳草绿。野花和钻天杨覆盖住这片原野。雨后,森林里的蘑菇连片拱出地皮,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我们围坐在堤坝顶上,狂饮故乡老酒。小春感慨:“朝如青丝暮成雪。五哥,不要剃胡子,让它长到耷拉地。”哎呀,兄弟,能活到地老天荒?咱共同举杯吧,把美好的祝愿送给家园:“风从河道走,跃过果树园。白天晒蓝布,夜晚浇农田。”
(作者单位: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