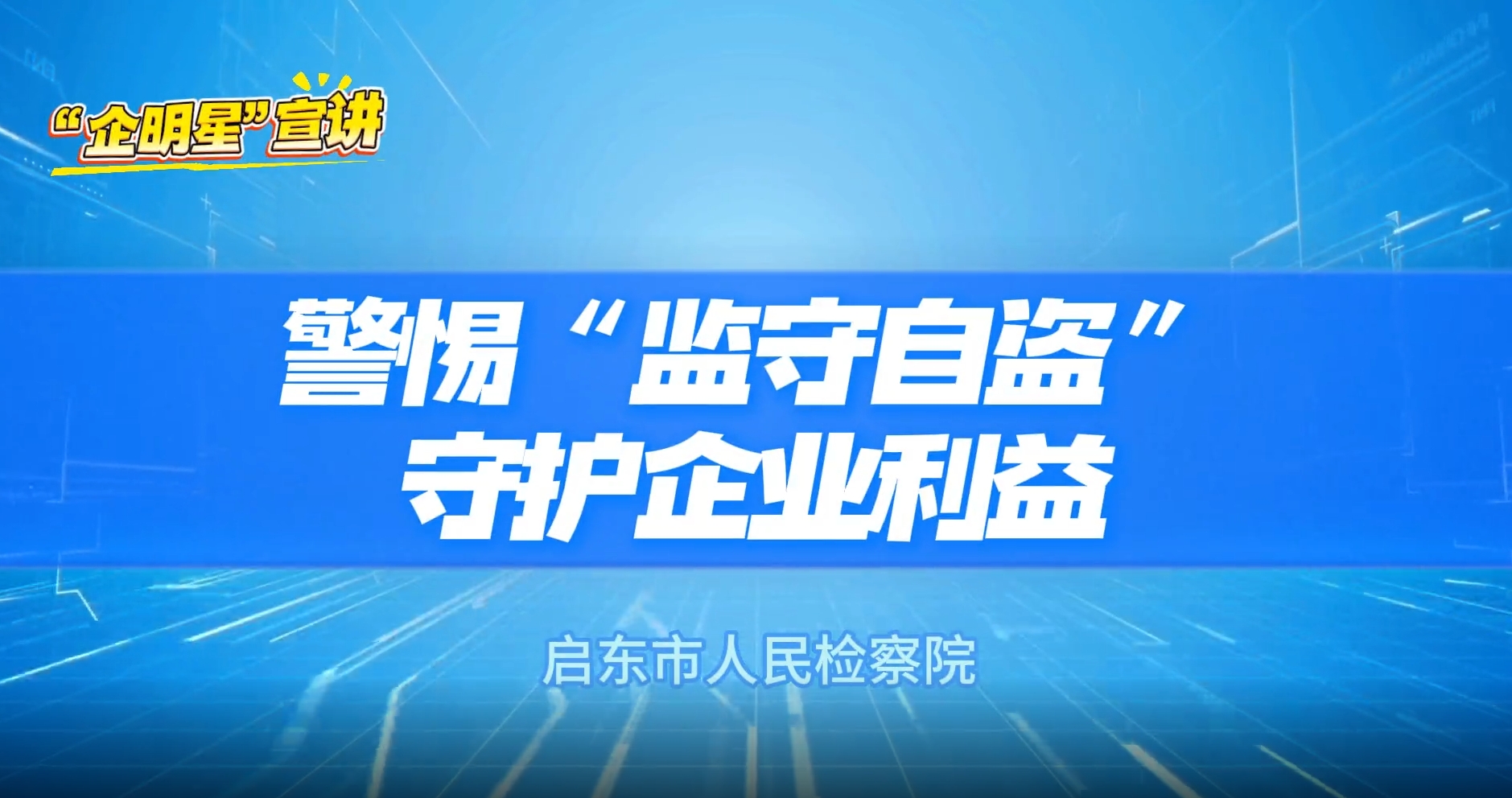除了好莱坞电影里的大毒枭和街头的黑帮火并,我关于哥伦比亚的所有认识都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包括波哥大,如果不是马尔克斯曾在此读书、工作、生活,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我在波哥大和一个哥伦比亚年轻人聊天,他说,马尔克斯更喜欢墨西哥,你看,他常年住在墨西哥城。这也是很多哥伦比亚人对马尔克斯颇为纠结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除了文学,马尔克斯没有给哥伦比亚贡献更多,他甚至都不住在自己的国家。而马尔克斯故乡小镇上的人甚至说,当作家他赚了很多钱,本可以花些钱铺路或者建一些卫生所的。他们显然希望,这是一尊彻彻底底的他们自己的神;达则兼济天下,这个“天下”当然得是哥伦比亚。
到哥伦比亚之前,我把这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大若干号的马孔多,因为马尔克斯就是这么写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盛产香蕉,《百年孤独》写了香蕉种植园事件。哥伦比亚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发生,有人可以坐在毯子上飞上天,有人一出现就招来无数的黄蝴蝶。马尔克斯写到很多次咖啡,但没有强调哥伦比亚的咖啡有多好,我就没当回事。我照着平常的量来了一杯,几分钟后问题来了。
当时刚坐到中央大学的演讲台上,觉得心跳的节奏突然变了,像老火车被迫提速,上气不接下气。哥伦比亚的朋友曾提醒我注意波哥大的高原反应,我说谢谢,哥们身体好,如履地平线。我在演讲中如实说到了“气短”,他们就笑了,那是咖啡的反应,难道你不晓得哥伦比亚的咖啡很厉害吗?原来如此,马尔克斯没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来波哥大谈文学的。因为《百年孤独》,我念大一时,打着手电在集体宿舍的被窝里写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在梦中穿过沼泽,醒来看见脚上还沾着泥巴,浑身上下浓重的淤泥味怎么洗都去不掉。为了得到《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我以定价的16倍赔给了图书馆,身上的钱不够,临时找同学去借。讲这些年马尔克斯对我、对上世纪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的影响。讲马尔克斯去世的那天早上,我给报纸写的纪念文章。在哥伦比亚驻华使馆马尔克斯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主持人摘引了那篇文章中的观点:
“在当代,大概很难找到另一位作家像马尔克斯这样能够对全世界产生如此持久和显著的影响力。1982年获诺奖以来,他就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此后,每一年诺奖揭晓,尽管新科状元走马灯地换,你都会在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看到另一个同样闪光的名字——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你总会在潜意识里用他的成就和标准来比照新得主。就像我们提到19世纪以来任何一位别的作家时,都会让他们的身边站着一个托尔斯泰,我们不乏阴暗地想看一看他们和托尔斯泰的肩膀是否一样高。在这个意义上,别的作家可能只得了一次诺贝尔奖,而马尔克斯获得了自1982年以来的每一届诺贝尔奖。”
我来哥伦比亚是朝圣的。但在波哥大,你不张嘴去问,很难在日常细节里看见马尔克斯的巨大荣光。而在智利,你在城市的街巷里游走,一不小心就可能在街头涂鸦中看见聂鲁达。哥伦比亚人当然引马尔克斯为骄傲,他们一遍遍问你,他们家的马尔克斯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马尔克斯尚未全面渗透进波哥大的日常生活。因为大师还不够古老?或者他们还没来及消化一位超级大作家?
走在波哥大的街巷里,因为缺少行迹指南,我只能想象大师在我落脚的每一个地方都走过。半个多世纪前,那个落魄又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里寻寻觅觅。走街串巷,朝圣依然落不到实处,我想起通常的好办法,买纪念品。问了很多人,哪里有卖马尔克斯的小雕像。事实上哪里都没有,该逛的地方都逛了,该问处也都问了,一无所获。
终于有人说知道,国家图书馆附件有家书店,那里有个马尔克斯文化中心。五个街区外。纪念品在书店的收银处。女收银员绝大多数时间都低着头,只用凉飕飕的眼睛余光看人。没有雕像,只有印着马尔克斯头像的冰箱贴和贴着老马头像的便条夹及木头镇纸。做工都挺简陋。这就是马尔克斯文化中心?好吧,聊胜于无;价钱却贵得稍显离谱,便条夹一万比索,边长不到4厘米的正方体镇纸一万五千比索。付款的时候收银员依然板着脸,看来这世上没什么能让她笑了。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马大师呢,我忿忿不平,只好去看老马的图书专柜:他写的,写他的,各种版本的作品、传记、研究著作、影像资料。我觉得舒服了一些:大师要有大师的样子。买了一本精装的纪念影集,抱着书跟一展柜的书合了影。帮我拍照的店员长一脸黑亮的络腮胡子,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