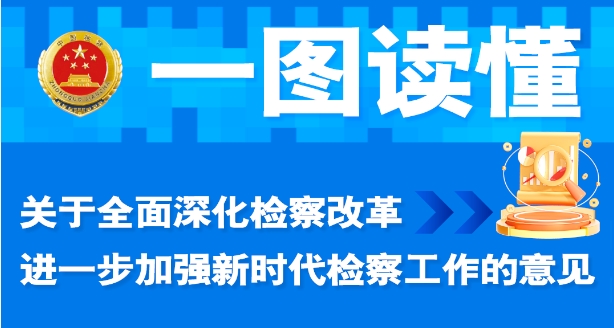《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他写作上的一座里程碑,几乎创造了当代小说受欢迎的奇迹,不但发行量在当代小说中名列前茅,而且受到各个阶层读者的欢迎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活着》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经典性文本。《活着》说服了众多的也是各阶层的读者接受它,那么必定具有某种独特和动人的魅力。而《活着》的魅力与该文本的叙事艺术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活着》的成功得益于它叙事手法上的成功。
《活着》讲述的是死亡故事。在这些死去的人群中,没有一个是该死的,如果一定要有人死去,那么该死的就是故事的聚焦人物福贵。因为他曾经是多么的邪恶啊———瞒着父母,把田产、房子等所有的家产都赌光嫖尽了;父亲被他活活气死了;他对妻子又打又骂……。可是这样劣迹斑斑的人不但没有死,奇怪的是还没有被读者所厌恶。就算他在最邪恶的时候,读者也对他恨不起来。我们不禁疑惑作者余华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术做到了这一点?回答是:余华通过叙述“控制”了读者。这就是“控制读者”的策略。要让读者接受小说里的人物,必须让读者对人物,尤其是那些负面性质的人物产生“同情”和谅解。余华在《活着》里运用的魔术正是这样的策略。
共鸣性
作者在叙事故事的过程中,注重了情节的共鸣性。说服读者同情人物,尤其同情那些让人厌恶的人物,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而比较恰当的“进入”的方法便是让这样的人物充当叙述者,因为这样的叙述方法可以控制叙述内容和方向,控制读者的感受。
福贵又嫖又赌,照理我们读者会对其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可是余华却让我们随着福贵的逻辑进入了他的思维视角,让我们从“嫖妓就是撒尿”、“赌博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的舒坦”等福贵式语言中体会着他的体会,幸福着他的幸福。总之,余华在《活着》里让一切都通过“我”去做、去看、去说、去想,以此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构建了“我”与读者的亲近关系,从而来“说服”读者,让他们依据“我”所叙述的一切来认识“我”、理解“我”,进而同情、原谅、宽恕“我”。“我”这样的内视角叙述为说服读者、赢得读者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当掩上书时,一份沉重的伤感从四面八方把读者笼罩进去。在不知不觉中,读者陷进作者所构造出来的故事中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活着就意味着永不放弃。对于福贵的感情也悄悄地产生了由鄙视到同情再到钦佩的变化。
近距离性
《活着》采用叙述中套叙述的叙述策略来拉近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是指读者与人物的一种信息契约,即两者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信息共享”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作者精心的不断调节来的)。
小说的开始设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整天“拖鞋吧哒吧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的民间歌谣收集者,将福贵引到现场之后,变成了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变成了这部小说的记录者。从福贵的自我讲述中,福贵的命运轨迹渐渐地呈现出来。表面上看,作家似乎站在作品之外,以一个高傲冷峻地姿态描述,冷淡地对待主人公所面对的一切苦难。而实际上,叙述语言的客观效果追求和叙述者的姿态背后却隐含着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这是一种“在之中”的呐喊,如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承受了巨大的悲痛时,往往哽咽难以说明,这种悲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去描述。
作者余华曾道,“社会力量来自道德上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又是由信息管理的技巧而非由正直的道德来控制的”。福贵的一生几乎概括了中国百姓的全部经历和一个国家的一大段历史,很容易地激活读者关于这方面的记忆。“福贵”与普通百姓的记忆是一致的,“福贵史”与他们了解的“国家历史”的记忆是一致的,因而一种“信息契约”的关系就自然地产生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也不断地被拉近了。读者终于认可了福贵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于是“同情”便油然而生。
广泛性
福贵年轻时候劣迹斑斑,可是我们却觉得都可以理解和原谅;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可以痛恨的责任人,我们无法对这部小说的任何人产生仇恨,里面的所有人物都让我们同情。余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我看来,《活着》设置的理想读者不是一类,而是多类,是一个面向各阶层的一篇作品。大炼钢铁和“文革”是为对政治感兴趣的读者准备的;战乱和土改那部分,是给老人准备的;有庆的长跑和读书为《活着》赢得了大量的学生;凤霞和二喜的爱情则是给无数婚姻疲倦的人带来了遐想和温暖……
因此余华的《活着》获得的赞扬从初中生到大学教授,从民间到精英,各色人都有,几乎人人喜欢。
诱导性
读过《活着》的读者大部分在一开始就被吸引了。开头讲述了一头老牛,这头老牛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名字:二喜、有庆、家珍、凤霞、苦根,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牛”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字,作者的用意在哪里?读者就会因为思索而放慢阅读的速度。这样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也就被大大地调动了。从而诱导读者思考阅读下文。
再有,作者并不急于讲完这个故事,而是娓娓道来,通过转述者“我”与福贵谈话的中断,使故事更有可读性,使故事显得漫长,适当的停顿是为了迎接高潮,真是钓足了读者的胃口。
寓言性
《活着》是一部阐释“ 活着” 的寓言, 是一部描写生存镜像的寓言。死亡是一个永恒绝对的存在, 是我们不愿面对而又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而死亡, 这个结果的存在, 恰恰凸现了“ 生” 作为一个过程的内涵。《活着》告诉了人们,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文中福贵没有因为凄惨的一生和凄凉的晚景而拒绝生存, 他以自己韧性、乐观的精神承受并超越了一切的灾难。这样的精神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而给读者带来心灵的洗涤。
人物配置
考察《活着》里的人物配置,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浪子福贵———浪父———赌徒沈先生———龙二;
壮丁福贵———老兵老全———娃娃兵春生;
丈夫福贵———爱妻家珍———下一代夫妇(二喜和凤霞);
父亲福贵———父亲春生———父亲二喜;
平民福贵———队长———县长春生;
老年福贵———老牛;
讲述者福贵———听者“我”。
在上列的《活着》“人物轴”关系图中,福贵始终处于“轴心”的位置。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福贵发生。死亡与苦难似乎包围了福贵的一生,而正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设置,体现了整部作品的主题,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中心人物,将故事人物更加紧密的串联了起来。